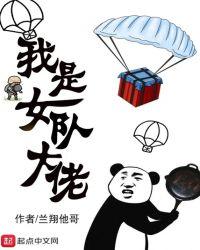嘉捷小说>重生之彪悍小跟班 > 第八十六章 悲惨世界推荐第一天(第1页)
第八十六章 悲惨世界推荐第一天(第1页)
()可发出声音的人是宁翔天,这个可恶至极,心里恨之入骨的男人,再好听,她也不愿意搭理。
大理石与木拖鞋发出的清脆声音很快消失在楼道间,回应这对母子的只是一声闷重的关门声。
门被关上那一刻,冰儿的心也跟着隔绝在这个家里。
她依然是孤单的,依然可怜兮兮的只是一个人,所有的疼痛和伤痕都需要自己慢慢舔舐干净。
丢下包,一个人坐在冰冷的地面,双手抱着膝盖,把头埋在里面,心却静的出奇。
房间漆黑一片,似乎黑暗才是自己世界里的主色。
人生酸甜苦辣四种味道,她只是短暂的尝试过甜味,却从小都是浸泡在苦涩的塘子里,想起身,已经浑身是苦难了。
心脏砰通跳动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,慢慢变得悠长而动听,心口那口压抑的痛处让她无法自拔。
进屋到静坐,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,冰儿都没有想要打开灯,只是像只鸵鸟一样缩着头,慢慢思考人生,想想接下来要走的路。
客厅里那对母子干瞪眼地互相看着,袁雪菲那张火红的嘴唇依然张扬地呼吸着,她唇膏的颜色总是妖艳得透着血腥。
“想什么呢?别一天天关想那些没用的,有这个闲心就多关心关心公司。”袁雪菲一边磨着指甲,一边慢悠悠地说着心中的不满。
从门响到楼上门关上,宁翔天拿着报纸的手就一直保持着那个姿势,甚至眼神的渴望毫无掩饰的暴露出来。
母子连心,虽然袁雪菲一边看着电视,一边磨着指甲,但是那双狭长的丹凤眼总有一股余光瞟向儿子。
知儿莫若娘,说的就是这个理。
自从那晚和儿子摊牌后,袁雪菲又开始新一轮的谋划,总想除掉这个碍眼的女人。
“你说什么呢?”宁翔天气恼地放下报纸,一个人走上楼。
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,我不可能答应的,你这是乱?”袁雪菲看一眼厨房煮宵夜的吴妈,硬生生把“伦”字咽下去。
这个词分量太重,在事实不清晰,不明朗时,她只能堂而皇之的警告着儿子。
又是一阵大理石和拖鞋发出的清脆响声回应着这个无理的女人,宁翔天根本不愿搭理这个女人。
虽然这是自己的母亲,可是他长大了,是独立的个体,分得清谁是谁非,无理取闹的把戏已经过去。
小时候被她怂恿着欺负冰儿,他没有办法,重要的也是无知。
慢慢长大了,懂事了,天儿针对冰儿的种种做法,只是为了引起她的注意,想让她别把自己关得这么严实。
适当的放松和交际可以让心灵轻松一些。
现在宁家在他手里,他更想彻底征服这个女人,甚至不管外界舆论,有种想娶她的冲动。
只有趁着自己在位,拥有一切主动权,速战速决,解决了冰儿,再慢慢征服她。
宁翔天站在冰儿的房门口,犹豫不决,抬起的手迟迟不愿敲响这道隔绝一切的门。
“天儿,你站那干嘛?”袁雪菲张开那张大红唇,森冷地叫嚣道。
>>
女人明锐的直觉总能轻松捕捉到儿子的行踪,猜出儿子的心思,看着儿子心神不宁地走上楼,不用猜也知道他想干嘛。